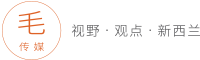广场上的风筝
从 1989到2016 ,27年过去了,可当年许许多多的感受和经历,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 。

作者:毛芃
自1989年6月4日那天起, 6月4日就再也不是日历上一个普通的日子,就像9·11 会触痛很多美国人的心一样,6·4也成为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心中永远的痛和难以摆脱的心节。
从 1989到2016 ,27年过去了,可当年许许多多的感受和经历,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 。
那一年,我刚到深圳工作不久,广东话还听不太懂,在那座年轻的城市里,做着年轻人才会有的快乐的梦。
6·4之前,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已旷日持久,全世界人的眼睛都盯着北京,我和周围的朋友们天天魂牵梦绕似地观看香港明珠台和翡翠台的相关电视新闻报道,因为是那样地如饥似渴,广东话也因此而“速成“。
可就在那样的时刻,鬼使神差我被公司派往北方出差,我悻悻地踏上旅途,因为离开深圳,就再无法看到香港电视台的新闻报道。
没想到这趟旅行,让我对6·4有了近距离的感受。
旅途中先回到我的家乡洛阳。这时广场的学生运动已经被定性,戒严已经开始。驻扎洛阳的一支部队要调往北京。听到消息,很多市民前去阻拦军车北上。我们家的楼下也贴着一张告示,呼吁居民们赶快参加阻拦军车的队伍。
记得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哪儿人多往哪儿钻。夏天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息,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深夜回来的路上,从一家酒吧经过,有年轻女人在里面唱卡拉 OK,又尖又嗲的歌声从夜色中飘来,我的同伴 – 一个年青的帅小伙子- 愤愤地“呸“了一声 :“商女不知亡国恨!“
6 月4日那天,我在开封。在亲戚家看到电视新闻节目中的通缉令,一个个学生领袖的照片出现在电视上。我的表弟 – 一个一向顽劣、让大人头疼的少年 – 盯着电视突然冒了句:“要是他们谁跑咱家来,一定得把他们好好藏起来!“
数日之后,我到了青岛,在离栈桥不远的一家旅店里办理入住手续。旅店前台女工作人员先是仔细盯着我看,然后向她办公桌一侧的墙壁望去。我顺着她的眼光看去,原来,墙上贴着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们的照片。
其实,我是不需要去北京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去北京,就是特别想去,那儿有我两个好朋友,都像我一样年轻。
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里空荡荡的,我坐的那节车厢有时候只有一、二十个乘客,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罕见,因为那时铁路交通是人们的主要长途旅行工具、火车上总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
天黑了,好心的女列车员过来同我聊天,她说:“都什么时候了,北京的学生都忘外跑,你怎么还往北京去。” 显然,她把我当成了学生。
北京火车站,许多军人在执勤。我的行李遭到军人的严格检查。不知是所有的乘客都被一视同仁遭此对待,还是只有看上去像学生的人受到这种“礼遇“。
在北京,一个美好的黄昏,我最要好的女友陪我到天安门广场。夏日夕阳的余晖下,广场显得空旷、静谧,有几个人在悠闲地放着风筝。 我眯着眼睛望着着天空中自由飘荡的风筝,几乎难以想象仅仅数天前这里还汇聚着全世界的目光、聚集着汹涌澎湃的人流、人潮……
看到一个老者收起风筝,我走上去问他是否能把风筝卖给我,因为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喜爱放风筝,于是想买个风筝送给父亲做礼物。
老者看了我一眼,“这风筝是自个儿做的,不卖。“
大概我失望的眼神让他有些不忍,老者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包里还有一个新的,可以给你。不过,广场上现在不能聚群儿,咱们换个地儿说话去。“
老者说着话,提起包就大步流星往广场外走。我愣了一下,友人急忙拉起我跟上老者,我边走边四下张望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终于又回到了深圳。一个周末,到一位熟悉的阿姨家吃饭。听阿姨讲起最近单位里人人都被要求对6·4事件表态,然后听她长叹一口气:“文革都过去十来年了,人们还得被迫说违心话、说假话。“
阿姨的长叹,让我不寒而栗。
从89年到现在,快20个年头过去了。当青春不在,偶尔,青春的记忆会闪现脑海。
有许多事情,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文 2007年6月发表于新西兰《中文先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