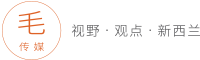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影评】弄真成假与传统吃人:《金陵十三钗》的两大致命伤
作者:(新西兰)张静河
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大多很叫座,但张导的作品、特别从事商业大片拍摄以来的作品又常为人所诟病,其原因在哪里?我想闪亮登场、速赚十亿的《金陵十三钗》或许是一个有意思的范例,能帮助我们弄清张艺谋作品的独特成就、美学特色以及常见的严重缺陷。
《十三钗》被导演认为是多年来难得的好片,拍摄四年,精雕细琢,投资6个亿,仅在艺校中海选演员就不下二万人。如此大阵仗,自然有很多看点:
- 效果震撼而干净洗炼的战争大场面;
- 玉墨与殡葬师之间爱情的发展与救人的主线相互纠缠、相得益彰并因此构成了主干遒劲而枝叶丰茂的叙事模式;
- 简洁朴实的对话的运用。如浦生临死前与豆蔻的对话表现了社会底层人物卑微而善良的心愿;
- 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伪善在日军大佐教堂弹琴的场景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 对烟花女子的性格习惯、动作姿态与日常对话把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得惟妙惟肖。她们眼角上挑的化妆尤其符合其职业特点,我们不知道当年的秦淮女子是否真地这样化妆,但它的艺术效果是如此逼真传神;
- 众妓女最后为女学生演出的一曲《秦淮景》,绕梁三日,凄美悲壮,把妓女们舍身救人的决绝与生命的鲜活,心灵的美丽推到极致。

《十三钗》充分体现了导演一贯的电影美学思想:力创纯美的视角画面、借助商业大片的哄动效应烘托崇高的主题,从而使其作品产生史诗性的厚重与张力。从《红高梁》借助民俗文化形式唱响一出生命礼赞,到《英雄》一改传统剌秦故事的叙事模式,让剌秦者与秦王都为了“天下苍生”而自愿背负道义的枷锁,特别是《金陵十三钗》,借妓女舍身救学生的故事宏扬人道救赎与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精神,其美学思想无不一以贯之。
为取得这一效果,导演充分显示了他驾驭电影语言的能力:大场景被处理得简洁纯净又具有震撼效果;矛盾冲突波澜起伏而张驰有致;叙事模式里浸透了历史的厚重感;优美绝伦的音乐和舞蹈把剧情渲染得更加凄美哀婉;以主观性极强的写意手法与细节高度逼真的写实方式相结合、强化对人物个性及其命运的关注;娴熟地借用民间文化、民俗仪式或戏剧化程式强化视角效果、创造独特的艺术真实。电影中多次出现的那面巨大的红十字架旗帜,在现实的教堂中是不会有的。当日军在教堂中追杀学生的危急时刻,约翰突然展开大旗抵抗顽凶,完成了他作为旁观者到拯救者角色的转换,那面旗帜作为一种意象-正义与天良的象征与假牧师教堂救人的行为融为一体而构成感人的艺术真实。
《十三钗》尤其体现了导演对纯美的追求,借助艺术形式的美,其创作意图被角色逐步诠释出来:男主角约翰因积极拯救无辜而获得人性的升华 ;孟书娟的父亲通过拯救女儿与其同学而完成了洗涮自身污秽的灵魂的救赎;妓女们为救女学生集体赴难,其品格崇高而神圣。众多的牺牲铺垫了纯真少女们冲出绝境走向光明的道路,这已经超越了“人道救赎”的一般意义,揭示了饱受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与走向新生的内涵。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画面优美情节感人的大片,看过以后却感到不可信,这是为什么?虽然编导竭力创造艺术真实再现历史真实,但全部逼真的铺垫只为粉饰一个过度拔高的主题,终使故事失真。
电影是以文学描写与摄影技术合成的手段再现生活的艺术,任何艺术再现不可能完全复制生活,即使再优秀的电影也难免些须“失真”的瑕疵。《十三钗》中失真之处并不少见,此处谨举二例:
A. 场景失真:李教官为救女学生在废墟中布了许多手榴弹,即使他有百步穿杨的神技,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能打中第一颗即属幸运,可是枪声响处手榴弹一颗颗打爆,侵略者血肉横飞。如此打法,那点日本兵早就杀完了。
B. 情节的失真:豆蔻为给死去的浦生弹一曲琵琶,要回原住处找琴弦,于是和香兰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被日本兵重重包围的教堂。如果这么容易出逃,还用得着费尽心思救人?香兰冒死潜出,只为找一付耳环,动机不能令人信服。
不过,《十三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此类硬伤,其表现手法总体上的弄真成假与创作思想上的传统吃人才是它的致命伤。
《十三钗》以弱者舍身拯救弱者的壮举体现人道救赎与民族自我救赎的主题,不可谓立意不高;以南京沦陷的血与火为背景,衬托少女求生的挣扎与献身的决绝,场面不可谓不震撼。每一个细节的精雕细琢都为了再现历史的真实或表现艺术的真实,主创人员不可谓不努力。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最后却因为主角的思想境界和人格被人为地拔高—拔高到远远脱离现实的地步而前功尽弃。
这似乎是当代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记得四十年前的一部畅销的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由于把一个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塑造成身无瑕疵的当代政治领袖,从而失去了艺术生命。张艺谋的电影似乎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局限:《英雄》中的刺客与秦王在生死悠关时首先想到的是 “拯救天下苍生”;《满城尽带黄金甲》在欲望与阴谋的宫廷权力斗争中赞颂的是“不自由毋宁死”现代精神;《十三钗》中一群妓女为了与自己素昧平生的女学生免于失贞而集体舍身赴难。尽管画面大多非常逼真、情节铺垫也很自然,但到了不合逻辑的结局出现之时,观众会立即感到这个结局的造作、虚假与粉饰,所有的努力便成了弄真成假。
不论历史上是否有过众妓女救人的记载,电影里的舍身赴难是相当不可信的。
电影中一干人对女学生冒死拯救,其救人的性质并不相同。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责任的救赎,天性的救赎与志愿的救赎。李教官及其兄弟作为军人肩负保国安民的社会责任,同胞有难挺身而出,特别在打红了眼的战场上,是很自然的。陈乔治长年受着天主教为爱献身的教育、为了不辜负养父的临终嘱托而乔妆赴难,责任在身,亦能讲得过去。孟书娟的父亲救女儿则是出于当父亲的天性。如果说殡葬师为情或色去救玉墨,从人的天性上讲是讲得通的,但一个耽于酒色的二流子式的人物突然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英雄并且不顾一切地去救学生,角色转变是否太突兀了一些?至于十二个妓女为了女学生免失贞操自愿送给兽兵蹂躏甚至是自愿赴死,除了一个小蚊子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拒绝这种牺牲,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生命对于个体来说,其重要程度无以比拟。妓女这一群体,以情色换生存,对世情、人情、爱情的虚伪性比任何人都看得透彻,因此,对自家的性命的重视也超过常人。剧中玉墨要让人知道妓女“重情重义”,要改改妓女自古以来所背的“无情”的骂名,带领全体妓女自觉自愿地为女学生赴难,编导的目的是要突出玉墨等妓女品格的高贵,而这种突出因过度拔高而导致了其行为的不可信。
除了过度拔高人物思想境界导致弄真成假以外,该剧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带有“传统吃人”的色彩。
悲剧的美学内涵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在命运不可调和的情境里遭到毁灭,从而引起悲悯与心灵的净化。《十三钗》是一部战争悲剧,其中自然少不了对无辜生命的杀戮与毁灭。但一个导演,仅仅只靠安排死亡来解决矛盾推进剧情,其导演水准就得打问号。如果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凭所谓的人的贵贱来决定人物的生存与否,就不仅仅是导演水平的问题了。
为了突出人道救赎之艰难,该剧对死亡与毁灭的安排过于轻率。若按电影中提及的动机,豆蔻与香兰的死是不会发生的。设想当时的情境,死亡并不是最恐怖的事,真正令教堂里的避难者恐惧的是满街的兽兵以及他们随时会施加给自己的不可知的比死亡还要恐怖的灾难。在这种情势下,豆蔻竟然为了让死去的浦生再听一次琵琶而离开避难所、穿过日本兽兵的重围去找琴弦,更不可思议的是香兰只是为一付耳环而与之同行,最后双双受辱殒命。
孟先生被日本军官枪杀,编导似乎是想让他“以死谢罪”来完成一个汉奸灵魂的自我救赎,或者说编导是想摆脱“同情汉奸”之嫌而用这最简单的方法抖开的一个戏剧包袱。依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在“汉奸决无好下场”的政治概念左右之下安排的结局。实际上,孟先生在那个场合下死于一个日本军官之手,是极不可能的。孟先生是一个熟悉当地情况、日语流畅、有文化有知识的汉奸,这样一个人在南京沦陷之际,对侵略者来说,其重要性甚至要大于一队士兵,日本军官会因为他要求女儿不被抓去赴晏而杀了他吗?
至于十二个妓女舍身赴难,则更暴露出编导者受到了“传统吃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早在三百多年前,杰弗逊就在美国《独立宣言》发出了“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人权宣言,人无高低贵贱之分,这在当代社会已是世人的共识,凭什么十二妓女就必须代教会学生赴难?在生命的天平上,妓女与学生的价值没有丝毫差别。而我们的编导几十年来饱受中西文化的薰陶,显然不会不懂如此浅显的道理。然而,当日本人要求全体教会女学生去参加侵略者的庆功会-显然是要去充当慰安妇的角色,编导此时的艺术处理,便是让剧中人全体行动牺牲妓女以保全学生,似乎少女的贞操比妓女的性命更重要,妓女的身份则比学生卑贱得多。
更有甚者,编导循着“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思维方式,把十几条鲜活的年轻生命轻飘飘地送进了屠场。剧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众妓女赴难之前,摔碎了镜子,每个人的怀中都藏了一块利刃般镜片,并且悲怆地宣言:“我至少要挖出他一个眼珠子。”由此表达了决死的意愿。
不客气地说,这是强奸了妓女的意志。
作为妓女,她们长期遭受男人的玩弄,忍受着全社会的甚至自己的精神上的鄙视。她们几乎失去了除生命以外所有宝贵的东西,以忍受侮辱换取生存是她们一贯的生存法则,活着,是许多妓女惟一的生命述求。因此,即使她们愿意以自己受辱去拯救学生,在完全绝望之前,她们决不会以自杀来追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境界。至少,十二个妓女中绝大部分人不会如此轻生。
再看前边一个情节,香兰在遭到日军轮奸之时拼命咬伤兽兵,因此被刺身亡,那鲜血喷溅的画面配上刺刀捅入身体的噗噗声,令人的灵魂为之颤栗。
编导安排这两个情节,本意是要表现侵略者的惨无人道与妓女宁死不倔的民族气节和高贵品格,让她们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升华。实际上,这种安排恰恰暴露了编导者心胸的狭隘与残留在意识深层的传统观念:女性只有以自己的鲜血才能洗净失贞的污浊,以性命抗争性侵的女性其品格才显得高贵。这与宋明理学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贞洁观有何两样?说得直白一点,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沉痛批判的“传统吃人”现象在现代电影中的再现。
回溯中国文学史,文人历来有赞美妓女的传统。苏小小坟、薛涛笺的传说赞美的是妓女的才华与美丽;李湘君血染桃花扇、柳如是力邀钱谦益投水殉国,歌颂的是妓女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董小婉、小凤仙为人所称道的是她们志存高洁、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至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的投水自尽,那是一曲旧时代妓女追求爱情的悲歌,是一个倔强的女性在对爱情绝望之时对封建门第观念的最后抗争,沉宝后自沉,既是那个特定人物性格的典型表现,亦是那篇明代传奇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一种完美的艺术真实。
《十三钗》中的妓女对自己结局的选择不论与上述哪一个故事相比,都没有其命运和性格发展的必然性,编导者强加给角色的命运选择、因为不符合叙事模式的内在逻辑发展,大大降低了这部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我为一部好电影带着这两大致命伤上演而婉惜,更为主题至上的固疾影响了导演的艺术才华而遗憾。
(201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