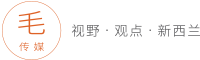一张中国脸的她坚信:“我无疑是个德国人”
她从小在巴伐利亚农村长大,却因为自己与亲友长相迥异而困扰。她是被德国家庭收养的华裔孤儿,到了中年终于辗转找到了亲生父母。她把离奇经历写成了书,读者却还能在书中感受到几十年前德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氛围。

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一对来自香港的新婚夫妇五十多年前在慕尼黑留学,产下一名女婴后却匆忙遗弃、踏上了返程航班。这名孤儿后来被一对德国夫妇收养,并且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环境中长大。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她成年后学习了中文,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在40岁左右踏上了寻亲之路。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霍尼女士(Tinga Horny)的亲身经历。
“我的父母是德国人,但我原来的亲生父母却是中国人。所以我有中国人的外貌,但是我的想法是德国人的。”在德国北部小镇博尔德斯霍姆的家中,霍尼女士对着德国之声的话筒,用中文慢慢地说道。
其实,霍尼在60年代刚出生时姓丁(拼作Ting),养父在这个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字母,创造了一个德语中独一无二的名字:Tinga。记者在开始采访前专门询问该怎么称呼,她笑了笑:还是叫霍尼吧。
社会变迁
采访的起缘自然是霍尼女士在一年前出版的书《送来的女儿》(Die verschenkte Tochter)。除了自己的离奇经历,霍尼还在书中花费了不少笔墨来描述数十年前德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状况。在德国之声记者眼中,这是书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您问我如今德国社会和几十年前的最大不同?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六十年代的社会相当均一,很少有不同的人。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感觉到社会气氛很友好;因为外国人太少了,所以大家都不排外。而七十、八十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兴起,外国人多了,社会气氛当然也就慢慢起了变化……”
霍尼女士自己也是记者,为德国《时代周报》等多家纸媒撰稿,几年前还曾在《焦点》杂志社担任过一个编辑室的主任。谈起全球化、排外之类的话题,她自然是滔滔不绝,从英国脱欧、德国右翼政党的崛起一直讲到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不过,她并不认为如今的德国社会变得不再友好,”只是如今外国人多了,不再显得特殊了而已。我们的社会显得更多元了,大家的好奇心自然就小了,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过程,不能和’友好’混作一谈。”
霍尼对德国之声记者说,她从孩提时代起,就特别反感他人故作惊讶地说”你的德语说得真好”。”我得一直和别人解释,我为什么有黑头发、为什么说德语。我现在还特别烦一件事:一旦中国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立刻齐刷刷看向我。可我是德国人啊,习近平好坏,关我什么事?”
身份认同
而这,也是她在青年时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困惑的一个主要原因。周围人尽管对她很友善,却始终视她为异类–完全就是因为长相;养父母虽然给予了她家的温暖,却受困于时代局限,无法理解她内心的困惑。霍尼终究意识到,她无法除去身上的中国人标签,于是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大学里学习中文,后来更是飞赴中国,求学工作多年。
“八十年代的中国,让我最惬意的就是我不再惹人注目了。很多人总是想与众不同、引人注意,但我从小就不是这样。在80年代初的背景,我终于找到了孩提时就想要的感觉–正常人的感觉!我骑着自行车跟着大家前行,只要我不开口说话,根本不会有人来关注我,这是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霍尼对记者说,在那个年代,其实已经有不少西方人开始学习中文了;”但是我学习中文的动机和他们显然不一样。学了中文之后,我能更好地了解这个给我贴了标签的国度,而且,就像您在书中读到的那样:要是我不会中文,我也无法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血缘不重要
十多年前,霍尼女士踏遍欧洲、东亚、南美,终于找到了她的亲生父母,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身份问题上,血缘真的不重要。”我的家就在德国,我的父母就是德国人。如今,我能够很平静地接受我有德国思维和中国外貌。我知道我有一个温暖的童年,而现在也终于找到了一个清晰的身份。”
在这之后,霍尼很少接触中文;直到最近几年,她又开始重拾中文。”我还记得80年代的北京,那时的中国人真的很率真,直接对我说’你的中文真烂’。而到了2000年之后,我再去中国时,至少在北京等大城市,再也不会有人对外国人感到惊奇。中国也像德国,经历了全球化,只是速度更快。”
(源自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