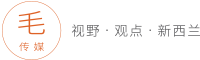一个零零后留学生的自白:我16岁,这是我第三个回不了家的除夕
坤灵不但学习成绩好,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对教育、对人生都有很成熟、很透彻的想法,别的小留学生在他这个年龄上可能还在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方法而挣扎,坤灵已经有了他清晰的人生计划并且付诸了行动。
我以前也写过留学生,但从未有哪个年轻人像坤灵这样引起我这么强烈的兴趣。这不仅是对一个少年人如何成长的兴趣,更是对新西兰教育体制下能造就什么样的孩子的兴趣。
在刊登对坤灵和他就读的奥克兰Parnell College的校长采访前,先刊发一篇他今年2月14日中国农历大年29写的一篇文章 – 《我16岁,这是我第三个回不了家的除夕》。
– 毛传媒

何坤灵同学 (毛 芃 摄影)
我16岁,这是我第三个回不了家的除夕
( 奥克兰 Parnell College ) 何坤灵
14岁时,我第一次独自过年。
那个新西兰的夏夜,洋人寄宿家庭的Party还在楼下继续着。我默默掩上房门——小床挤在书桌的一侧,校服塞在床尾的衣架上。狭小的房间,此时骇人的安静。
墙上没有年画,门旁没有春联;角落里,蜘蛛还在织着自己的网。不知怎地,新西兰的夏夜竟如此寒冷。
与父母通完了电话,我披上自己的汉服,轻抚膝上的古琴。小窗外看不见月光,我无言地伴着琴声吟唱: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李白《关山月》
那夜,我睡的很晚。
作为低龄留学生独自在外的这两年半,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依靠。
每周与父母通话的时间有限,聊的最多的自然是生活中的阳光与欢笑。有时,当电话对面熟悉的声音悄然静默,掩在内心深处的寒意就会止不住的淌出眼角。
从最开始面对英国文学的绝望,到现在斩获剑桥文学考试的年级第一;从最开始被孤立、被排斥,到现在朋友遍布全球;从最开始生活的苍白,到现在排满日程表的精彩,这一路上不管有多少寒夜、多少风雨,都只能自己默默扛下。
一个人的除夕夜,只能茫然地凝视着床头的天花板,思绪在模糊的记忆中漂流。
记忆里的除夕,永远是值得怀念的。
但我怀念的并不是年味——在我的记忆里,年味早已褪去了色彩。
没有热腾腾的饺子,没有令人掩耳的爆竹。虽然依稀有些烟花的炫彩,和厨房里老家腊肉的飘香,但这些就和年年照旧的春晚一样,只在记忆的烟雨朦胧里化作一团昏黄。
除夕的晚上,客厅被暖炉烘得格外热和。我们三人把煮熟的腊排准备好,配上刚刚上街买来的卤肉、蛋烘糕,围坐在炉前。
母亲给自己的高脚杯里乘上白葡萄酒,父亲则在橱柜里寻找他珍藏的佳酿。我不知自己喝的是什么了,也记不起三人谈笑的话题。只知道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笑了很多。
除夕让我怀念的,是不管窗外如何的风霜之冷、人情之寒,当我们一家三口团聚时,总有那涌上脸颊的温暖,驱散一切的寒意。
2018,我独自过的第三个年。
学校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国际视野,希望我来组织初中部的“中国年”主题活动。
我专门叮嘱同在学生会的同学们:鼓励非华裔小朋友参加,让他们主动去探索陌生的文化。我期盼着,这样的尝试能带来更多跨种族、跨文化的交流与友谊。
申请本科所需要的准备渐渐堆积了起来,我只能在打磨申报哈佛的文件之余,挤着时间推进自己的教育创业项目。
过年回不了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我知道,每一篇发布的文章、每一天朋友圈的分享,只要我继续努力成长,就算再不起眼,我的父母都会为我骄傲。
这样,他们的除夕才能更温暖。
16岁,不知还要独自过多少个除夕。
家人相聚的场景,也从过去暖炉围坐、把酒长谈,变成了手机上微信视频的小窗。
从小不断的搬家,早已让我对离别麻木了。但独自在外我才明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房间、一个城市,而是那两个与我生命相连的人、以及我与他们的共同记忆。
外面的世界,或许还在风雪交加。回不了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未尽的工作,默默为我们共同的记忆添上一笔精彩。让家里的除夕,尽量温暖一些。
但是我很清楚,我们三人怀念的,从来都不是那暖炉的热量。
我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