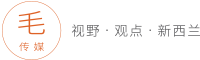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访谈】淳子:张爱玲裹着一层壳,美利坚文化似乎没有丝毫浸入
讲座结束后,我对淳子女士进行了采访,下面是采访内容实录。

淳子在讲座上 / 毛芃摄影
淳子:喜欢张爱玲,一定是有原因的。记得第一次看张爱玲,就像胡兰成第一次读张爱玲,一开始是懒散着读,可读着读着就坐直了。读完了心里还诧异,怀疑自己的审美是不是出了问题,然后再读一遍,心里有了确认,确认张爱玲是我所有阅读经历当中独一无二的作家。

奥克兰有很多“张迷”
我自觉是能读懂张爱玲的,能读出她文字当中的“夹缝文字”。是因为我们是同城女子吗?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我想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记者: 张爱玲的文章中有很多对三十年代上海市井风情的描写,那是老上海骨子里的东西。您作为上海人,怎么看这一点?
淳子:张爱玲文章中的那些上海文化、上海风骨,上海味道,就如她所说,是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等我们死的时候,它再死一次。
上海这座城市至于张爱玲,就如同都柏林至于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巴黎至于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伦敦至于(英国作家)狄更斯。
张爱玲是一口井,你去打捞,捞上来的是一座城。
假如有一天上海毁灭了,我们可以凭借张爱玲的文字拼贴出一个上海。
记者:做张爱玲研究您是采取了什么方法?您说是沿着张爱玲生平的足迹走了一遍,去过她在美国居住的公寓,去过她工作过的美国大学,甚至还去过胡兰成当年逃难到温州的住所。
淳子:我做张爱玲研究使用的是最笨的办法,我是沿着张爱玲的足迹,一个个的走过去,一遍遍地走过去。这个行走的过程,也是解读张爱玲作品和她本人的过程,这是一个体悟过程,它是有心灵温度的。有人评价说,我的文字是用脚写出来的。
记者: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去香港时没告知她的弟弟,出国后也不再联络与她关系最亲密的姑姑。她在亲情上何以表现得这么决绝?
淳子:张爱玲临走时和姑姑相约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因为怕牵连姑姑。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如果你有海外关系,在大陆是有麻烦的。如果你有海外关系在美国、在台湾, 有可能会被当作特务关押起来。张爱玲不联系姑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她为什么对弟弟如此绝情,还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中把弟弟往死里写,这牵涉到张爱玲对她们家族男性的看法。张爱玲觉得她们家族这些清朝高官的后裔、就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永远也长不大,她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对这类贵族男子有过精心的描绘。
还有一个原因是,张爱玲认为她弟弟是属于她继母那边的人,她必须站在母亲和姑姑这一边,和弟弟划清界限。

童年时的张爱玲和她弟弟张子静
淳子:张爱玲是带着她的《秧歌》,带着她在沦陷区文学的盛名,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地去了美国,但美国并不是她的“应许之地”,她写出的大量英文作品几乎都没有被出版社所接受。她最寄希望的英文作品是《少帅》 (Young Marshal),当她把这个作品拿给一些汉学家看,汉学家都说看不懂。她自己说:“好像七八个话匣子开在那里,各说各的。”
淳子:是的,《少帅》是以张学良和赵四为主要人物和线索的,她想写一本中国的洛丽塔,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相遇的时候,赵四只有14岁。
在这之前,张爱玲写的所有英文作品都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她便把宝押在《少帅》上。她准备写十章,写完七章后,拿给那些对中国背景比较了解的专家看,没想到大家都说看不懂。
这部作品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越写越不喜欢张学良,连带也不喜欢赵四小姐。
张爱玲本来是想写到“西安事变”就作结的,结果没有写完就突然收笔了,是写不下去了,这本书自然是没出版。
《少帅》是在她去世后才出版的,这是生者对死者的重新挖掘。

记者:张爱玲是个文学天才,她没有实现自己的美国文坛梦,心里一定挺失落吧?
淳子:张爱玲对自己进军美国英文文坛的失利,或者说是那种尴尬的境地有自己的说法,她说:“我想写的,都是别人不要看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张爱玲来过美国吗?》 。张去了美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可她所有的创作素材、写作手法,都是原封不动照搬她在上海时的写作素材和写作手法。她是浑身裹着一层壳的人,那个美利坚文化,似乎没有一丝丝的浸入。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吊诡或是悖论。张爱玲离开上海、离开大陆,逃亡美国,是想实现美国梦,她想更自由地写作。当她来到能够自由写作的空间和语境的时候,她的作品却没有人接受了,这是张爱玲最大的尴尬。
记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张爱玲,张爱玲可曾有过任何回忆两人感情的文章?她和胡兰成的婚姻给她的写作带来过积极影响吗?
淳子:张爱玲活着的时候,对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没做过任何公开回应。不过在她去世后发表的自传性小说《小团圆》中,全面地回应了胡兰成。

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部小说中,她对自己也是毫不客气的。
这段婚姻给张爱玲带来的满是伤痛。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诀别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爱你了,是因为你先不爱我的。”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委屈。
接下来她写,“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了,我将只是枯萎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离婚后,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思绪常常一片空白。
张爱玲在美国有过身孕,可她第二任丈夫赖雅不愿要孩子,他们找私人医生堕胎。堕胎之后张爱玲躺在浴缸中,当水浸满全身时,她忽然想起胡兰成。堕胎之后那种痛苦的状态下想到另一个男人,可见胡兰成带给她的是怎样一种噬骨的痛。
记者: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几岁,她第二个丈夫大她二十多岁。张爱玲对男人的选择同她个人的身世、童年时代的生活是否有关系?
淳子:张爱玲说她只对中年以上的男人有感觉。她在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座谈会上说过,男人应该要比女人大一点才好,因为男人是喜欢被崇拜的,而女人也只有在对男人崇拜当中,才能维持更久的感情。所以无论是胡兰成还是赖雅,都符合她对男人的年龄界限。
从她固执的寻找中年男子的情感或心理路径出发,可以指认张爱玲是有一个死穴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恋父情结。
2005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花过两个课时讲张爱玲的恋父情结。

张爱玲与赖雅
记者:张爱玲在美国花了10年时间研究《红楼梦》,她的那本评红楼梦的书您怎么看?她的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淳子:对于张爱玲这样的作家,自由应该呈现于写作之中。看了她的红楼梦研究,说实在话,她的研究有些让人费解和失望。
大约张爱玲太爱《红楼梦》了,她的文章呈现出呓语般的状态。感觉她还是带着传统红学的镣铐跳舞,跳的很吃力。如果她能像她柏克莱大学的上司陈世襄教授那样,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来研究,可能更有光彩。
(注:陈世襄是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张爱玲是接受他的邀请到该校中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记者:您在讲座中说张爱玲去世时还有30多万美元的遗产,可她晚年却过着极简的生活,几乎是家徒四壁。您怎么看待她这种生活方式?
淳子:我感觉张爱玲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受了梭罗的极简主义的影响。
你知道梭罗同爱默生关系密切,张爱玲曾经翻译过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的作品 –《爱默生选集》。那是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后在香港翻译的。
1967- 1969年,张爱玲作为作家和研究者在哈弗大学呆了近3年。哈弗在波士顿,爱默生就生于波士顿,还是哈佛毕业;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1862年)也是在哈佛读过书的。
因为这些人文地理的因素,张爱玲在文字上、思想上和哲学上应该同爱默生和梭罗有过比较深刻的接触,我推测梭罗的《瓦尔登湖》所表达的极简主义对张爱玲是有些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梭罗说过这样一句话:“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谓的舒适生活,不仅可有可无,甚至可能会阻碍人类升华。”
不过我最能确定的是,张爱玲的极简主义来自她对人世的看破,这个看破就如同《红楼梦》的贾宝玉,出生于一个豪华庞大的家族背景,眼见如此一个大厦哗啦啦倒塌,宝玉于是披着一袭猩红的斗篷出家了。《红楼梦》是张爱玲一辈子最爱的小说,她在《红楼梦》中能看到自己家族的历史,能体会到那种悲辛。

童年时的张爱玲同她父亲和弟弟合影
记者:张爱玲的作品至今还有很多读者,全球都有“张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对张爱玲的评价,中国大陆同香港和台湾之间是否有区别?
淳子:张爱玲和她的作品能够到现在还有众多读者,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简而言之,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这是大陆许多作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海外学者是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张爱玲,并且给予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作家的地位,大陆学者则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给予她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