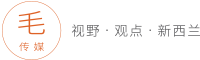珂珂: 一个坚强达观的女性
作者: 毛芃
2019年3月5日上午,传来珂珂因癌症去世的消息。这虽是意料之中,可我还是忍不住震惊和伤感。

珂珂全名冯蕴珂,英文名CoCo
(廖小雪提供图片)
我是2月14日情人节去医院看她的,那时她走路已经需人搀扶,然而说话中气十足,眼睛也是炯炯有神。
我知道她患了癌症,不治之症,已经放弃治疗。我没问她的病情,说些不相干试图能让她放松的话。不料想她主动说了一句,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生老病死,早晚得来。她说得那么淡定、平静,我一下不知怎么接她的话。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把包包忘在病房没有拿,因为头天还有其他人去看她,她不知道是谁拉下的。她还告诉我马上就要转院去Middlemore医院,我说那我过几天再去医院看你。
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生老病死,人间常事,但一个你熟悉的人离世,这个冲击还是不一样的。 一整天,我都无心做其他事情。脑海中尽是珂珂的音容笑貌,我在电脑中翻看过去给她拍摄的照片,阅读她从前发我的文章,在我手机上的“朋友圈”中寻找有关她的零星记录。
朋友们都在悼念她,都说她是个好人,一个好脾气、好心肠、善解人意的好人。的确,珂珂待人实在是没的说,在道自己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她还是热情接待不知情的国内朋友来她家小住。照料客人的起居饮食,对正常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她自己是个需要人照顾的癌症患者啊!
记得有一年去北京,返程时从北京转机香港,正好珂珂当时在她香港的家,她约我在香港玩几天。原本晚上10点多落地的飞机晚点3个小时才起飞,降落香港机场的时候已是夜里一两点了。珂珂半夜三更来接机,我很过意不去,可她见到我满心欢喜,没一句怨言。在香港的几天她天天带我四处逛街看风景,还带我登上香港最高楼环球贸易广场,在顶楼的餐馆喝咖啡。

一次我夸珂珂的丝巾好看,她随后在国内买了这条颜色类似的丝巾送我
我的电子邮箱中,至今保留着2010年12月同珂珂的通讯记录。我那时大概才认识她不久,因为我在邮件上说:“很高兴认识你!”
就在这最初期的交流中,珂珂就叮嘱我:“要注意身体, 不要重赴我的旧辙。”
珂珂告诉我,她的身体弱是年轻时工作太拼落下的病根。她多年前做过一场大手术,死里逃生,她感概她的命是捡回来的。
也许是这个原因,珂珂的生活格外充实,对什么都很有热情。
我的电脑中,保留着珂珂2012年参加我在奥克兰北部Golf Harbour一家酒店举办的旗袍派对的照片。 那个派对一是为了好朋友们在一起热闹开心,二是为了奖励一下我当时主办的同人网的作者们。
记得要买一些小礼物作为奖品,珂珂和我一起去Briscoes ,挑选一些精致的生活用品和小装饰品,她帮我用彩纸把礼物一个个包好。

旗袍派对上给珂珂发小礼物

旗袍派对上的走模特步游戏,这是珂珂出场
珂珂是个懂生活、有品位的人,家里布置得雅致漂亮。当年,几个喜欢写作的朋友常在她家聚会,大家海阔天空地聊天,聊历史,有很多开心的时光。
珂珂喜欢写作,也喜欢画画,多年前还拜画家穆迅老师为师。她家客厅的画架上,总有一幅还未完工但看起来已经是很好看的画作。
 珂珂和好友林太太在自家客厅外
珂珂和好友林太太在自家客厅外
(毛芃摄影)
那时候的珂珂勤于创作,虽然文笔还不是那么老道,但文章浸透着她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她不是风花雪月、岁月静好派, 她的文章有很强的写实性。
也许还有奥克兰华人记得几年前飞凡剧社上演的话剧《偷心》。这个话剧就是以珂珂的短篇故事《小偷》为蓝本加工、改编的。 故事描述了老一辈华人移民同年轻一代华人的生活冲突,反映了海外孤寡华裔老人的生存状态。话剧上演后,在奥克兰华社引起不小反响。
下面这段话是我2016年11月看这部话剧前发在朋友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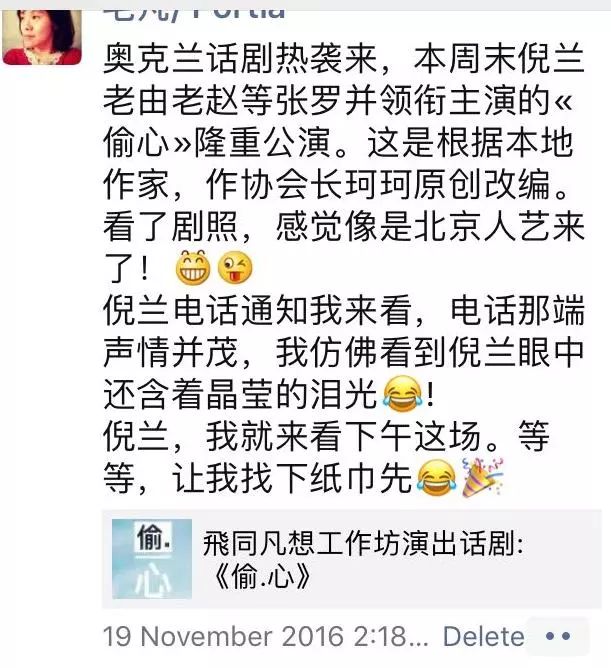

《偷心》剧照,左边是老赵主演的独居老人
珂珂是2014年担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长的,她是从前会长大卫王手里接过这一职务。珂珂自担任会长之后忙碌了许多,要出版协会刊物,要请国内的文化人来演讲,一年总有几次请理事们在她家开会,每次都准备好水果茶点招待大家。
记得她请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来过,请内蒙作家郭雪波先生来过。虽然只是做个公开讲座,但这前前后后的各种联络、接待、组织、宣传,陪同,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珂珂同作协理事在奥克兰接待舒乙先生

珂珂(右)向听众介绍郭雪波先生
珂珂做过大手术,身体一向瘦弱。可她自担任社会工作忙碌起来后,人倒比过去精神很多。从2014年开始,她共担任过三届新西兰华文作协会长,每一次,她都聘请她信得过的人做理事,每次,她还颁发委任状,弄得很有仪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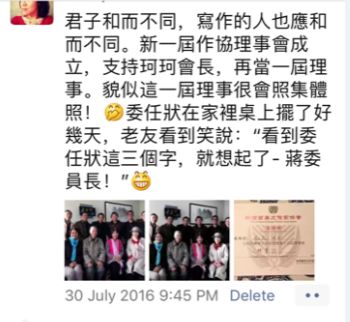
这是我第二次接到委任状后写在朋友圈的话。

2016年,新西兰华文作协新一届理事合影 (前排右二是珂珂)
珂珂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华文作协的工作,她还在新西兰华人环保教育基金做义工,还担任了新西兰国际妇女会常务副会长。

珂珂同国际妇女会的会员们合影
(廖小雪提供图片)
珂珂担任了更多的社团工作,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她人更开朗了,而且也白胖起来,显然她很快乐、很享受这方面的工作。
最近这几年我们见面不多,除了作协理事开会或是活动上见个面,平时各忙个的,但每年珂珂都会有一两次请我单独喝茶、聊天。
我喜欢珂珂,喜欢她的温和、包容,佩服她的涵养与修养。她算得上是有钱人,但她身上看不到一丝有钱人的毛病,看不到那种有意无意的炫耀、卖弄。
我的微信朋友圈上,还记载着我们2015年8月见面喝咖啡的记录,那天是在奥克兰东区Howick一个俱乐部,时值南半球的初春,正好是新西兰的水仙花节。聊天的时候,我顺手在朋友圈发了张照片,写了几句话。 结果,珂珂当即跟帖,不假思索写了几行鼓动大家购买水仙花支持癌症基金的话。



最后一次同珂珂单独见面是在2018年下半年,在奥克兰东区万寿宫喝茶。她说她的背疼了好一阵了,看医生也没有看好。她说她家的新房盖好了,花园里有太多的活儿要做。她以为背疼是因为在花园弯腰干活劳累所致,没想到这已经是癌症病发了。
我不敢想象当医生告诉她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时候对她是怎样的打击。她是接到医生电话一个人一大早开车去的医院,她肯定没料到等待她的是这样的晴天霹雳,身边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生活,有时候会太残忍,可无奈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珂珂等作协会员同作协老朋友曹玉堂先生合影。左起:大卫王、曹玉堂、曹小杰、毛芃、珂珂
我是很晚才得知珂珂病重的消息。情人节那天,我买了一束玫瑰和巧克力去看她。她精神看起来不错,身上挂着止痛吊针。说话的时候,她不停地用手去揉后背,说是背疼。
珂珂走了,她不用再遭受病痛的折磨,给朋友们留下对她无尽的思恋和怀念。
我多希望能有机会再对珂珂说声“谢谢”,感谢她对我所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