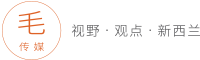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评论】一个新极权主义国家的诞生和结局
作者:凯波(德国之声客座评论)
极权主义体制的政治恐怖、僵化意识形态、统制经济和政治虚伪会造成社会结构的退化和停滞。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历史决议,不仅宣告了一个新极权主义的诞生,或许也同时宣告了她的终结。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的人们大概很难相信,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和漫长的冷战之后,极权主义的幽灵竟然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太平洋两岸。北美大陆虽然在年初曾经侥幸躲过一场”啤酒馆政变”的危险,但是,随着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闭幕,一个新极权主义国家在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陆诞生了。
在上周结束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三百余人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上两次历史决议,分别发生在1945年和1981年,都经过党内充分讨论的民主协商和反思,通过对党的路线的拨乱反正为中共在两次历史转折点把握时机创造了最大范围的党内共识,堪称中共其实用主义理性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典范,也是中共能够保持长久活力和韧性的诀窍。
自我加冕的”悄悄革命”
相比之下,第三次历史决议虽然自称要从中共百年历程中汲取经验,整个决议却形同东施效颦、照猫画虎,企图效仿六届七中全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的理论权威地位、继而为他在七大上确立绝对权威铺路,通过本次决议树立起习本人的理论地位,但是既未经过充分的党内讨论,没有任何自我批评,不敢否定任何先前路线(特别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折衷主义,在一个封闭的会议中借着对党的百年历程的肯定,自我肯定了习过去执政的九年,犹如自我加冕一般完成了一次”悄悄的革命”,宣告了三十余年威权主义过渡的结束。
当然,历史上以执政党中央全会集体决议、一致通过的方式确立一个极权主义体制,虽然罕见却似曾相识。希特勒在1923年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历经十年利用选举和暴力窃取了魏玛民主;斯大林也是从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失败之后逐渐从”三人小组”中夺取权力,在列宁身后逐一清洗列宁的战友,直到1936年颁布所谓”最民主的宪法”,然后展开大审判,树立起从察里津神话到全面的个人崇拜。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斯大林就是一个从神秘帷幕后面走出来的独裁者,从”1936到1938年,设法使一个专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发展……在此期间,全世界与其说对他的力量、意志和深仇死怨感到惊讶,毋宁说对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惊讶”。
教科书般的极权体制
而这一切,二十世纪曾经出现的两种极权主义,居然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复活了,而且综合了左右两种类型,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完成了俨如教科书一般的极权主义体制准备,为明年的二十大、也就是习的第三、第四、甚至终身连任做好了意识形态的准备。

首先,这种对所谓百年党史的历史主义迷思,几乎就是19世纪以来曾经统治德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的翻版,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安东尼所说,是黑格尔所称”存在就是合理的”庸俗哲学的无限延伸,是”欧洲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所留下的痕迹”。无论左右何种极权主义,他们所本的历史主义都是反智的,无视一切个人尊严、嘲笑一切人道主义、启蒙运动和自然法,不是用历史而是用历史话语背后的政治强力取代道德良知,也就是机会主义的和反历史的。
其次,”决议”对”两个百年”的民族主义和时间差的机会主义论述,几乎成为修宪之后为领导人连任寻求意识形态支持的唯一借口,也掩盖了这一决议所标志的两个重大转向。第一个转向,不再坚持任何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而是全面代之以民族主义的”十个坚持”,在不放弃共产党名号的同时转型为一个极右的民族主义政党,这也是江泽民时期”炸馆事件”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2012年”915″反日运动的自然结果。
而极端民族主义在经济层面的体现,不会简单停留在自力更生、解决卡脖子技术等等口号上,还将体现在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私人部门的保留,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则实行从上而下的指令控制,如同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形态,并且迟早将正式转向战时经济体制,否则,难以解决市场经济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包括有产阶级对私有财富的担心和工业民族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转向,则是以确立习近平为全党核心、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两个确立”原则,正式取代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体制,不仅形成一个个人独裁体制,也掩盖了这一独裁体制对共和制度的破坏,为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即将转为事实上的现代君主制铺平了道路。
毕竟,在理论上,领导终身制与否几乎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唯一重要差别。对于成立在”五四运动”余波的中共来说,不能不说,百年之后对共和的颠覆不啻为对历史的莫大嘲弄。
红色怀旧:再造个人崇拜
其三,共和的危机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普通人来说,可能都过于抽象、难以体认,但是,如阿伦特所论述的,“权力出现危机之时,暴力就出现了”,借助最新科技的政治恐怖几乎是意识形态挂帅的最好伴侣。
这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文革时期极权主义运动所带来的群众恐怖,但在新极权主义下,第三次历史决议意味着他们正在从革命的神话走向反革命的暴政。一个无所不在、不受限制的国家暴力已经从过去九年针对公民社会、新疆和香港的不断镇压中成长,变为一个利维坦式的怪物,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历史的终结
不过,暴力固然催生了新极权主义,却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消解着权力,可能最终令领袖本人都感到危险,担心暴力机器的坐大反噬着政权本身。这在今年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已经成为最大的变数,连带着引发政治效忠的难题–所有人都可能被怀疑为”两面人”的危险。这本来是新极权领袖九年前加强个人集权的初衷,如何防止出现”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局面,却在集权完成后促成了预言的自我实现:不仅政法系统内部需要展开整风运动,即使在六中全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负责起草的笔杆子们面对记者其呆板僵化,形同僵尸,完全丧失了表达能力。这或许才是中国意识形态战狼化面具下的真实一面。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预期,中共的二十大后将迎来一个的不仅是一个新极权主义体制,而且还意味着世界格局正式进入到新冷战,极权主义所支持的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阵营将围绕着全球化和地球外空间展开长期竞争。
但是,极权主义体制一经确立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不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欢呼历史终结的回声,而是由政治恐怖、僵化意识形态、统制经济和政治虚伪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退化和停滞。新极权主义或许在短期内能够避免来自任何阶层的革命,但是长期而论,这就是历史主体的消亡也是历史的终结。
如卡洛.安东尼所总结的历史主义的命运,政治固然能够借助历史崇拜和政党崇拜塑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包括天才的幻觉,但是”领袖们的神圣性、大众追随他们的义务,其持续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运气和权力维持的时间”,一如”赶英超美”或者”东升西降”这类口号的结局,或者斯大林之死所意味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历史决议,不仅宣告了一个新极权主义的诞生,或许也同时宣告了她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