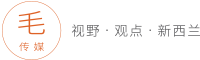李大光:一个不在右派份子名單上的右派 他临终前的行为是否该被谴责
作者 /(奥克兰)千玫 编辑 / 毛芃
8月18日,毛传媒发表了一篇网友千玫纪念她父亲的同事李大光的文章。文章中李大光在文革开初就和妻子寻短见并在这之前先杀死了两个孩子的细节,在网友中引发争议。另一位网友Judy H于是也讲述了她的一段亲身经历,说的是一位当年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文革时自缢身亡、死前杀死自己两个孩子。两个故事,有相似的背景、有相似的令人心碎的情节。……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两段悲剧,移民新西兰的网友们看法迥异。…… – 编辑
我父亲在1957年打成右派後,就像成千上萬與他有相同命運的人一樣,被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在那個天寒地凍、鳥不拉屎的地方,我父亲救過一個人的命,他的名字叫李大光。
那是他們到北大荒850農場勞改的第二年冬天。

严酷的北大荒 (网络图片)
一日,大雪紛飛,寒風刺骨,在外勞作一天的右派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農場他們棲息的地方,胡亂吃了些東西,就準備睡下。這時,我爸發現李大光不在,就問:“李大光呢?有沒有人看見他?”
那一天,李大光與管事儿的人吵了幾句,那管事的就把他分配到較遠的地方干活,脫離了平日一起干苦力活的難友。一天下來,誰都沒見他,也沒有人想到他。
那時農場的生活條件極差,環境惡劣,加之右派份子、勞改犯的身份,所有人都是前途未卜,情緒低落,自顧不暇,苟且偷安⋯⋯
我爸担心李大光怕是遭遇了不測, 就招呼幾個人拿了個裝土的筐子,沿著他們幹活的路線一路尋去⋯⋯
那晚,漫天大雪白茫茫一片,北大荒的冬夜寒風凜冽,氣溫降至零下30°C,他們一路喊著李大光的名字,一路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
原來李大光在收工回來的路上,因為大雪覆蓋整個地面,加之天色漸暗,看不清道路,掉進一人深的樹坑,摔斷了腿,無法自已爬上去,夜幕降臨,荒漠大地,北風呼嘯,雪越下越大,在樹坑裡疼痛加寒冷,幾乎失去知覺。這時,他想到了年輕貌美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為了讓自己不這樣死去,他咬破嘴唇努力使自己清醒,堅持,再堅持一會儿。就這樣,他隱約聽到我爸他們一行人的喊聲,他得救了⋯⋯
死裡逃生後,李大光在850農場面臨的不是醫治腿傷,而是上級領導的審問。
第二天,李大光沒有出工,被帶到大隊部的他,手裡拄著樹枝做的棍子,站在隊長面前,要求講述昨晚發生的事情,他拖著斷腿面對領導,木呆呆地立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突然,有人從背後猛踹了一腳,他猝不及防,倒地不起,臉貼著地面,動彈不得。
隊長說:“你這是真的還是裝的”,那種侮辱帶來的巨大憤怒使得他瞬間熱血泵滿全身,他用家鄉話罵了一句:“放你媽個屁!” 被羞辱的痛苦遠大過身体的疼痛,他沒了知覺,忘了身份,怒爆粗口,斯文全無!(這一段細節是李大光另一個朋友、司法部著名右派張玉根2019年對我講述的。)
在我的記憶中,李大光是比較瘦削的高個子,英俊挺拔,瀟灑自在,玉樹臨風,氣度不凡,既有男子陽剛之美,又有知識份子儒雅孤傲之氣。他早年遠渡大洋彼岸的美國,學習法律。畢業後在聯合國謀得一份翻譯工作。五十年代初,20歲初頭的李大光青春年少,滿懷理想回来报效组國,被分配在司法部工作,我父亲正是在那時與他相識。
家父湖北漢陽人,祖上經營布匹和大米,在當地也算是富甲一方。然時不假年,祖父家正值生意興隆、蒸蒸日上之即,日本侵華。武漢戰役那年,國破家亡,產業落敗,窮家富家,一齊奔上逃亡之路。
我父亲15歲那年,我祖父在我父亲的腰上系了一串銀元,送兒上路,由他自己去上海闯荡、读书。從此,武漢便成為他遙遠的故鄉,與父母只有在夢中相見。
戰亂時期,父亲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輾轉读大学,與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李大光在生活軌跡上本無交集。但是1949年後,他們人生的列車似乎奔去了同一方向,都到了北京司法部。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他們被劃為司法部的同一個右派小集團成員。這一年是中國舊曆丁酉年,他們戲稱彼此是“丁酉同科”。不得不說,在紅色恐怖籠罩下坐監犯科還能開出這種玩笑的也只有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了。
李大光從歸國到劃為右派也就是五六年的光景,他年輕有为,意氣風發,躊躇滿志,一路開掛,幾年內,成家立業,順風順水,成為司法部頂尖翻譯和史良部長的助手,怎料人生的高光時刻轉瞬即逝,到了57年反右,李大光以為自己人生跌入谷底,殊不知,那只是他厄運的開啟!
北大荒斷腿後,承蒙皇恩,他提前結束勞改生涯,回到了北京月壇三里河的家。然而,司法部解除了他的工職,家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一樓的大單元尚可棲身,但沒了工作,斷了經濟來源,怎麼辦?!他只能靠著給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作些英文翻譯維持生計養家活口直至1966年。
在那淒慘過活、勉強維生的四五年時光里,李家暫時獲得了安穩的生活。记得一次李大光得到一筆不錯的翻譯费,他破天荒地請一幫北大荒的難友去北京莫斯科餐廳開葷,那也是我第一次去莫斯科餐廳吃飯。
李大光聰明睿智且多愁善感,和藹溫潤下又天真多情。在我五六歲時,聽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至今難忘。他的家鄉懷寧是黃梅戲發源地,那裡山青水秀人也俊美,十七歲時他去鄉求學,第一次離開生養他的小山村,爬過山崗,趟過小河,在江臨渡口,遇見了一位美麗的姑娘。那女孩面孔白淨,梳著兩條粗粗的辮子,在江口撐小船接送過往的客人,看著女孩忙碌的身影,他徒生愛意,暗下決心,總有一天定要回來娶她為妻⋯⋯ 李大光後來說,當第一次見到宋媛(李妻)時,一眼就喜歡上了,無它,只因宋媛梳著兩條大辮子,長的就像那搖船的姑娘。
李大光天性浪漫豪爽卻又敏感多疑,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 先是邓拓的杂文《燕山夜話》和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罷官》被批判,接着是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被作为反党集团被揪出,李大光就嗅出這場運動比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为洶湧。
1966年5月份,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中共高官倒台,成为壓垮駱駝的稻草。李大光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每天都從西城到東城史家胡同我家,與我父亲說上幾分鐘話就匆匆離去。八月中,大約有一星期不見他來,我爸料他出了事,就打電話給李大光的父親。李父用低沉的聲音平緩地說:“他不在了”,我爸立即明白他是自我了結了。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不僅了結了自己,還了結了他那漂亮、溫柔、在北京72中教英文的妻子和兩個可愛儿子。
一個不甘受辱的靈魂就這樣淹沒在滾滾紅潮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些年,我在網上查遍了右派份子的名單,名单上有我父亲的名字,有許許多多熟悉的名字,但唯獨沒有看到李大光。
李大光是個小人物,是50萬右派分子之一,是巨大分母上的一個小分子!甚至可以說他是個殺人犯,因为他親手結束了四條生命⋯⋯
时光過去近六十年,我時常還會想起他。記憶中的他總是在笑,眼睛瞇瞇彎彎的,細密的皺紋刻在小麥色臉頰的眼角處,薄薄的嘴唇緊緊抿著,笑不露齒,落腮鬍須的淡青色顯得他瘦削的下巴尤為堅硬,他手持手杖,派頭十足,走起路來即使跛腳也是大跨步的。他抱著幼小的我,有時也會拖著那瘸腿背著我,唱著保羅·羅伯遜的歌走過前門大街、中山公園和東交民巷。
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史家胡同西口,那一年他四十二歲。
–
(注):李大光,安徽懷寧人。其父李平衡,早年留學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国首位國際勞工局理事。(Google可查)
【作者后记】紀錄李大光這段往事是我長期的心願,今年是他百年誕辰,于是就寫了这篇小文以寄託哀思,聊以慰籍其在天之靈。只因當時年幼,不諳世事,能記住的事情不多,本文是憑些碎片記憶和少數當事人的回忆写成的,實在有些差強人意。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们知道李大光这个名字,知道他悲剧性的一生;也真心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那個残酷的年代,了解我們父輩们的犧牲。

Dream
结局实在悲戚,令人难以释怀。
运动初始阶段, 李大光个人到底是遭遇了怎样具体的事由和压力,以致如此决绝地杀死挚爱的妻儿三口再自杀?或仅仅只是他过于敏感,由高层彭罗陆杨倒台而预知自身命运,彻底精神崩溃?
这里是不是千枚大姐出于某种原因有意隐去未做交代?难免让人物和故事的完整性受到一些影响。
向后人描述党国现代史,这种并非名人却个性鲜活的知识分子小人物之遭遇命运,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千枚大姐有心、费心了!
千枚
謝謝你的提問,這是個大問題,也是我父輩生前不斷討論的話題。據說有一份遺囑,現在看來有些荒誕,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是非常符合常理的。
北大荒回來後,李大光就一直都在說死的事,他曾說每次看到火車疾馳而過的時候,他每每都有撲上去的沖動,那時他已經心灰意冷了,所以文革剛剛開始,根本沒有觸動他毫毛,就帶著家人與他一同赴死。無疑他是衝動的,但也不能不說是經過他深思熟慮的,他一定是覺得無路可走了,也不想連累家人。
不同的人,思路是不同的。
任 之
杀妻、杀儿,再自杀。这种人也不咋样。自己不想活去自杀,那是自我选择。拉上老婆孩子垫背,妥妥的烂人。如果老婆孩子当年躲过了他的毒手,十年后也可以享受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说不定现在春风得意,安度晚年。
千枚
自殺也是要有勇氣的,誰都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上來就說爛人實為不妥。
我覺得大可不必在法律層面或用當今的道德準則來評判58年前的這啟慘案。
文革初期,李大光就人間消失了,當時,我家周遭幾乎家家被抄,戶戶受難,對李大光的事所有人都三緘其口,避而不談。75年後,他家的慘劇才漸漸浮出水面,三五好友一見面,就談論李大光,朋友們在惋惜他的同時也都認為他不該這樣做,认为这是軟弱的表現,尤其不應該帶走兩個無辜孩子。
對他的做法,大多數人其实是不認同的。李大光,他不是殺人狂魔,也不是自殺控,在北大荒那麼艱苦的地方他都堅強地活了下來⋯⋯ 他承受不起即將到來的衝擊對生命的打擊,他更不願意親人因自己而受過,他做了最決絕,最有效,也是壞的選擇。
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再回看那瘋狂殘暴非人性的時代,除了痛心,是不是應該多一些對李大光的包容和同情?
Benny
具体有什么原因触动他毅然决然地带着全家人去赴死呢?因为对整体社会形势的悲观吗?
Portia
一个人只有在极端的绝望、在生不如死的境地中,才会视死如归。
任之
自杀是个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但没有危害别人。杀人是剥夺别人生命,是犯罪行为。
文革中受迫害自杀的人很多,值得同情。但杀妻杀儿的行为不在可以被同情的范围之内。可以自杀,但不要逼迫别人自杀,更不要杀家人。
Portia
正常社会这么说没错,李大光是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高压下作出那样极端的行为。 与其谴责他不如思考造成这种人伦惨剧的缘由。作者无非是从人性角度展示那个恐怖年代知识精英的悲剧人生。
William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既要…又要”才是正确的答案,我们既要谴责他杀人的犯罪行为,又要追究逼疯他的社会原因。完全赞同,既然要杀人,那就去杀官员嘛,怎么可以杀妻儿?
千玫
再講一個我父亲告訴我的发生在北大荒的真人真事吧,那是個沒姓名,死在北大荒850農場的《北京青年報》的年輕人。
一个死在北大荒850農場的《北京青年報》的年輕人
我父亲他们到北大荒勞改的第二個年頭,早上每人發兩個饅頭就下地勞動去了,直到日落,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住的地方,十幾個人睡在一個大通舖上,洗漱用水都在同一個桶裡,解手沒有廁所,都要到戶外去解決,生活條件之差對他們這些右派來說还不是最難熬的,兩年下來,有些右派的家人應訊全無,無人關心,思念、焦慮和無望才是最難熬的。
有一個年輕人,就睡在大通舖我爸的旁邊,他剛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青年報》,不到半年就被劃成了右派。这位年輕人自到北大荒後就沒有收到過家信,在他生前的最後一個晚上,他用針線一邊補著破了洞的襪子一邊說:”真想吃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第二天早晨,大通舖的人醒來時,他已經冰冷了⋯⋯
“他就像熬干了的燈芯,就剩下最後一點點亮”我爸這樣形容。
這個年輕人沒有家人為他收屍,在那個年代,或許他的家人也在落難,或許家人不恥有這樣一個“不爭氣的孩子”,還或許⋯⋯。

1966年8月18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接受毛泽东检阅
众人聊到这里,Judy H 女士给大家讲了一段她的人生回忆。
Judy H
Judy 的回忆:留苏学生小王和小顾的故事
作者:Judy H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主人公是我的同事 – 女生小王和男生小顾,他们是一对50年代从上海派到苏联留学五年、之后分派到北京工作的夫妇。
小王和小顾是我老伴在留苏时的同学,他们都是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金属物理专业的。1958年毕业后,小王分配到我们的单位 – 北京研究院 – 工作,小顾分配到北京的军工部的研究所工作。据我老伴说,他们两位在苏联留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小顾。在流苏期间两人已经要好,但当时不鼓励留学生谈恋爱,所以也没有公开恋情。
回国后,小王和小顾就结婚了。因为小王和我不在一个研究室,我和她并不熟悉,只是经常在食堂见到他们夫妻二位,数年后,又见到他们可爱的一对孩子,一个约10岁的男孩和一位约8岁的女儿。小王和小顾都是上海人,都长得白净清秀,孩子更是可爱,漂亮又聪明。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王去了干校,而小顾据说是参加了军工部门的派系斗争,后来被关了起来。因为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小王也不在北京,当时反对派因为考虑小顾要照顾孩子,所以在下班后,允许小顾回家。这样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据说,小顾在那天从看守处回家后,带着两个孩子在外面餐厅大餐了一顿,然后回家安排孩子睡觉。之后他先后掐死了两个孩子(先是比较大的男孩,然后是女孩),最后,自己悬梁自尽了!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给吓懵了!当时小王还在干校,什么也不知道。单位派人去接她,不敢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只说是有事。回家后,可想而知,小王会是怎样的悲痛欲绝。
当时不少朋友说,如果小王不是在干校,她的结果也会同归于尽!就像上面讲的李大光的命运一样。
更惨的是,小王就此孤独一生,直至前两年去世。
我曾经和小王在一个干校相处一年,她很坚强,从来不提这事,白天也高高兴兴的,还打乒乓球。但有一天晚上,我被惊人的惨哭声惊醒,朋友告诉我,那是小王,那就是她在晚上独处时的真实心境。
我老伴告诉我,小顾在学校就是一位非常争强好胜的学生,样样都要争第一,比较孤傲。但是,即便是因为性格,也不至于自杀,甚至把至亲至爱的孩子 – 尤其是无能自保的孩子和弱者 – 杀掉。
我想,从道德和法律上,他无权、也无理这样做。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他当时已经认定对他和对他至爱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无望的世界,留着他们也是无尽的受罪,不如一起去吧,……。这是多么残酷和无奈的纠结。
事实也证明,小王的余生是非常不幸的。有权有势的部门和人员不会关心她,不会为她创造一些条件,让她能慢慢磨平创伤。记得我曾经和当时的一位负责人谈过,是否让小王回到上海去(户口迁移),因为她在北京没有亲人,而上海却有。但那位负责人对我说:“小王还没有转变立场,没有和杀人犯小顾划清界限,因为至今她都没有再婚。”
看看,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小顾后来平了反,小王最后老年痴呆,病死在北京的老人院,全靠同事朋友的安排和照顾。
这么多年来,每每想到小王和小顾以及他们的孩子,心里都是一种莫名的痛。
千 枚
謝謝分享,看到中途就有點知道要發生什麼,眼淚不停的流,那個年代的悲劇是現在的我們难以理解的。
任之
一个有家庭责任心的男人如果想自杀,不是把老婆孩子杀了垫背,而是应该先去买寿险,然后自杀,用自己的生命换老婆孩子能从保险公司拿一笔钱。做不到以命换钱留给老婆孩子,也应该自己一个人了断,别去祸害老婆孩子。
小美
那个年代, 哪来的寿险? 那是一个什么保险都没有的社会。
有梦人
站着……果真不腰疼啊!
在那个疯狂年代的那个政治氛围下,一个绝望之人从哪里生出这份天外祥云般的“责任心”?!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街头屠戮、棒杀师长、踏毙同僚都成了生活日常。那个习惯于你死我活命如草芥的社会,用现今的道法视角去审视个体行为得十分小心。
留恋
如果夫妻二人一同赴死,那么可能任之的问题就好解释一些。如果是一方要死,因此先杀害了家庭其他成员,那么我觉得也是过于残酷的,即使是在那个年月。
制度当然要谴责,但是制度不是唯一需要被讨论的对象。老舍和家人完全闹翻,自杀时也没去下杀手找人一起赴死。
Bernny
闹翻了就不会关心他们将来的困境了。那些决绝地在自我了断之前先了结自己最珍视的人生命的人,是希望家人不会遭受自己预见到的更加残酷的羞辱和折磨。
Judy H
现在去谴责那个自杀前先杀害孩子的父亲,我认为有点残酷!
能把人逼到要杀自己孩子的程度,想想那是怎样的社会压力!我们不谴责那个制度和社会而是那个几近疯狂的父亲?是否是重点不分、太过冷酷和严苛了呢?
我倒是认为,很多事要从当时的时代和环境来判断是非,如果把它简单地归到“杀人”,“垫背”,不如“买保险”,那就像现在去笑话“原始人为什么拿树皮野草围住屁股,却不穿裤子?” 那般可笑和无知。要知道真理超越一步就是谬误。反右运动中的那些死者都是牺牲品。
Galvin
用現在的三觀去考量那個年代的行為,屬於反向的刻舟求劍。
张博士
“在2016年8月末的一天,中国西北部阿姑山村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了她的名字:杨改兰。28岁的杨改兰被人发现和自己的三女一子死在户外。当局表示,杨改兰在给孩子们喝了农药并用斧头砍伤他们之后自杀。”这个年代依然有绝望的人。
太阳林
在那个荒诞、荒谬、荒凉的年代,有多少的悲剧我们数不清。这是人间的悲剧,从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千玫讲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如果不是当事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主人公背负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无法理解他对当下生活环境和未来的绝望。这样的故事留给我们是无尽的悲哀和同情……。历史不再重演!
有人说这是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能这么轻描淡写吗?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实属罕见。可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听见施虐者和助虐者们的忏悔,但我坚信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公义的审判,等待他们的将是永不熄灭的“火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