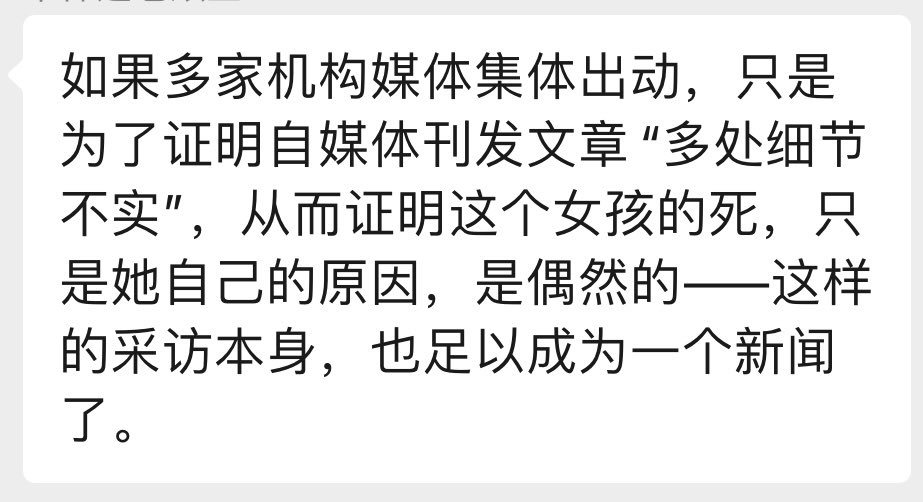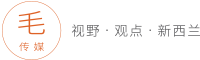谢天谢地,我们终于不太习惯饿死人了!
作者:魔鬼歌唱
(本文发表于8月22日微信公众号《下岗女工之魔鬼歌唱》,后遭删帖)
【民间疾苦里但凡参杂一丁点儿信息失误,就是弥天大谎,就是欺君之罪,而且这样认为的人越来越多…… – by 虚雨】

有篇文章说一个女孩死了,可能是饿死的,于是大家都鼓噪起来。
鼓噪的原因很多。例如西安方面意见很大:明明不是在我大西安死的,你文章里有事没事提啥西安?吓得作者方赶紧认错:我们没说清楚,对不起对不起。
再例如死者老家,宁夏某县,领导们紧急开会——已经有很多会要开了,这种计划外的会想想都心烦——然后对外统一发布:人是有这么个人,事是有这么个事,但文章很多地方不属实,至于哪里不属实,我们还在研究……
总之你要死尽管死,不要跟我们扯上关系。如果是某个历史名人,例如西门庆,那我们倒是要尽量去扯关系的。
以上还是官方,民间的鼓噪声就更大:GDP第二怎么会饿死人?假的!不信!
民间鼓噪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自以为知识分子)的口吻,例如这种句式:“充满对底层的想象与臆断”。
总之,这篇文章还是假的比较好,这样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官方不用计划外操劳,爱国者又揪出一群特务,知识分子们的质疑精神难得地赢了一次。像这种让方方面面都满意的事,现在真不好找了。
但这事偏偏是真的,至少权威机构说了有这事——就算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大家开始考据细节。
那位说“充满臆断”的,找出了很多条“臆断”,例如死者经济窘迫而住房租金不菲,“这不合常理”。
虽然作为一个资深底层,我怎么看都觉得,说经济窘迫就不能租好一点的房子,这特么才是“对底层的臆断”。
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写一个年轻人为了得到一个脑子短路的富家女而起心除掉现女友。这种事哪国都有,之所以叫美国悲剧,指的是事情曝光之后的美国式反应:媒体、政派生生把这事搅成了一堆烂污。
而这位女孩之死如果是一个中国故事,其主要内容也是在她死去之后,尤其是在这次死亡被讲述出来之后。
文章很快被发布方自己删了,发了个声明,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事是真的,但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事,反正流量也够了,还是删了吧。然后据说连号都找不到了,很显然,这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没有人欢迎这个故事:官媒气不过自媒体啥都敢发,自媒体气不过现在流量这么难搞怎么就让他们搞到了。但凡报销得起路费的媒体都涌向那个宁夏小县城探索真相:是不是读的211?考了几次公?骨灰扔哪儿了?当地领导如果不再提升,估计现在经历的就是职业生涯最大的阵仗了。
与其说是找真相,不如说是找假相:证明那篇文章不真实。死人这事是翻不了案了,但最好别的情节都不真实。我们不怕死人,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只是别的情节让我们不安——读了211也考不了公,考不了公就可能饿死,这个逻辑链破坏力很大,所以一定要破坏它。
于是结论就是:不是211、考公没考第一、骨灰没扔进垃圾桶,所以人虽然是死了,但是危害性并不大,大家可以继续岁静。正如前林副统帅所说:这么大个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
林副统帅说过很多话,数这句最正确。因为后来他也死了,死状甚惨,但大家果然都觉得不算什么,这么大个国家该怎样还怎样,直至今日。
有个朋友宽容地指出:那么多人在乎“是不是真的”,其实也是件好事。我觉得这也是个臆断。真实未必是好事,例如这个真相:致死率最高的东西不是饥饿,也不是某种癌症,而是愚蠢。如果大家知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蠢死,这个真相本身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如果蠢货们会羞愧的话。
反动作家王小波说过很多反动话,其中最反动的一句就是:这个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事了。
几年前,一位脖子上栓着铁链的女人不幸被发现,引起很多议论。当时我从那件事里归纳出了8条逻辑,其实可以再归纳成一条:在有关方面眼中,没有人,只有事。
现在这条逻辑依然好用,只是有关方面的范围大大拓展,包括各路媒体,甚至全国人民。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不在乎你死,但不喜欢你的死法!或者换个说法:那里确实有一滩人血,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喜欢有人吃人血馒头!
也就是说,只要把吃人血馒头的批倒批臭,人血也就没有了,这样既科学又卫生。
德莱塞给他的小说起名《美国悲剧》,是为了讽刺“美国梦想”,而所有的中国悲剧都应该是捍卫中国梦想的。那女孩的死法像个噩梦,让人不踏实。我们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让我们觉得还有路可走的故事。
例如西门庆——那才是能实实在在带来旅游收入的东西嘛!
所以,关于一个女孩死去这件事,现在已经指向一个妥善的结果。
此事的真正奇怪之处是:在方方面面的输出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正能量,居然被方方面面都忽略了。那就是:谢天谢地,我们终于不太习惯饿死人这种事了!

2
其实,我们吃饱饭的日子并不长。
35年前——这个数字据说在今年是个禁忌,至少在夏天是。谢天谢地,现在夏天已经快过去了——我刚进校读硕士。由于那个奇特的数字,学校有关方面召集我们开会,谈论加强领导的必要性。一位年龄很大的师兄发言说:“同学们啊,我是经历过饿死人的啊!我还抬过饿死的人呢。我亲眼看见,有些抬死人的,抬着抬着,自己就成死人了!”
虽然我当时年轻,也听出这发言似乎偏离了规定的方向。没想到师兄的结论是:“同学们啊,你们说,不加强领导,行吗?”
我被这位师兄的逻辑整懵了很多年。我还私下问过他:那些人饿死,到底是因为偏离领导,还是服从领导?师兄笑而不答。后来该师兄在学术界相当成功,估计和这种逻辑能力不无关系。至少,当后来听到有人质问“谁说饿死过人?你见到了吗”的时候,估计他是不会挺身而出,而是会笑而不语的。
所以,唯一确定的结论是:我确实年轻。
但我还没有年轻到不知道饿死人的程度。见是没见过,但亲身经历过——没饿死,是半死。
在我12岁之前,一种叫作“粮食定量”的东西规定我每天摄入的主食不能超过350克。当然,如果你认为“主食”的意思是另外还有很多有油水的“副食”,那你就太天真了。
所以,在整个身体发育阶段,我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作为成年人,我父母每天的“定量”比我多80克,他们尽量省下来给我,但终究有限。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哥进入初中,每天可以吃1斤零6钱——当时的有关方面终于承认中学生需要吃饱——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我分而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没有饿死,是因为我哥挑食。
也许又会有人说这是“臆断”:初中生还不如小学生能吃,这不合常理。但真正的常理是人和人生而不同。我哥虽然也是“底层”,但他没好菜就不想吃饭,当然,那个时代很少会有好菜。而我则天生酱油拌饭也能吃几碗。
我就这样在“定量”的光辉照耀下成长。定量体现为“粮票”,所以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辨识各种粮票:全国的、省内的、市内的、米食的、面食的、细粮的、粗粮的——后者的意思是,只能购入玉米或者番薯之类,这些都是被纳入“主食”范畴的。我见过大学教师的祖父和同为大学教师的父亲在一起吃了几天饭后相互仔细兑付粮票,也记得父亲有次用10斤半粮票从小贩那里换了一把竹椅,悠闲地坐在门前——那是一次成功的交易,没有谁认为这种生活不正常。
直到我聆听那位师兄关于饿死人的高论时,粮票依然存在,只是大家都不怎么用了。过了发育年龄才迎来粮食够吃的年代,那时我一顿饭通常能吃下12岁以前一天的定量。所以我迅速成了一个胖子。用现在常用的术语来讲,那叫PTSD。那时没有人知道PTSD,但我们这代人胖子特别多。
硕士毕业时,学院的大姐给了我一份“派遣证”,这意味着我被“分配”去了一个单位。同时给了我一份“粮油关系证明”,还有几十斤粮票。我说这些东西没用了吧?她说拿着吧,谁知道呢?
现在想起来,“谁知道呢”四字,是多么伟大的预言。
那几十斤粮票我一直没扔,当时只是随手收起来,现在看来,那是我成长年代最重要的证明:那是一份许可证,证明我被许可生存。
我岳母是个典型的中国持家女性,对“生存许可”有着本能的理解。所以她在那个年代一口一口地省下了一笔足以换取几十把竹椅的财富,以备随时可能来临的“灾荒”。然后,DUANG,粮票失效了。这是时代给岳母开的一个玩笑,但这只是玩笑的一部分。
玩笑的另一部分是:我们其实从未脱离需要许可的生活:许可结婚、许可离婚、许可生娃、许可不生娃、许可说话、许可沉默、许可发笑、许可哭泣、许可对某些数字的记忆、许可为了哀悼而摆下鲜花……
上述只是玩笑,但还不是笑话。笑话是:正如人们在需要粮票才能生存的时候对粮票这种东西丝毫不以为怪,他们对无处不在的种种许可也相当适应,甚至感到很舒适。当别人感到奇怪的时候,他们便鼓噪起来,群起而攻之,并取得胜利。
死去是不需要许可的,所以人们对种种死亡见惯不惊:跳楼的、跳桥的、在现代化城市的人行道上活活淹死的、挂在树枝上的少年、倒在大街上的老妪。但是,当一个女孩疑似饿死的时候,大家就受不了了。也就是说,死去不需要许可,但饿死需要。
结论就是,谢天谢地,关于饿死人的记忆似乎已经足够遥远了,就像“大批判”的记忆一样。人们大可不必像我岳母一样还随时担心灾荒来临——如果不幸还记得,也可以假装不记得,或者以某种特别的逻辑去记得,就像我那位师兄一样。
248年前,在北美有一群人宣布他们有一些生来就有的权利,例如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另一种语境中,这些权利被归纳为一条:生存泉是最大的任泉——这种权利当然不包括不写错别字的权力。
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有不被饿死的权力。如果再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有不承认你被饿死的权力。
3
在需要粮票的年代,我接受过很多关于英烈人物的教育。几乎每个英烈都有金句供我学习,甚至有一些英烈写出了整本的日记。但不知为什么,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刘胡兰小姐的临终遗言:
“我咋个死法?”
如果说粮票是我身体发育的注解,这句话就是我精神发育的注解。我们被教育得认为当烈士是最有前途的职业,而这种职业就免不了要选择一种死法。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法的选择越来越集中到一种:饿死。如果我成绩不好、如果我劳动不行、如果我身体不健康、如果我不会做家务、如果我不会礼貌地对待所有亲戚,那我就不会获得一份好工作,然后就会饿死。
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在死亡阴影中长大的,然后把这种阴影传给了我们的孩子。你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问问,他一定熟悉这个逻辑链条:成绩不好就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会饿死。
和我们的时代相比,这个链条只是变得简单和具体了,例如做家务和身体健康(体测所需除外)基本被排除,再例如考大学被具体化为考211,找工作被具体化为考公务员。
当我儿子在死亡阴影中成长到具备了一些起码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你们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考好大学和找好工作的吗?你们和大学以及工作单位是一伙的,专门为它们制造生源的吗?
这个少年哲学家的问题让我无言以对,我在苦想中甚至产生了去问问我父母的念头:你们在一个需要粮票的时代把我生下来,是为了让我分食你们的定量吗?
最终我和儿子达成了谅解:鉴于他已经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还是读下去,但是不必为职业发愁。他的职业应该是从人生中发现可以享受的东西,并且不用担心饿死。
虽然人生中的不享受远远多于享受,但儿子还是决定原谅我们,因为他发现了我们是爱他的,就像我发现了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一样。
我不知道那位死在出租屋的女孩,她的父母是否爱她,各种鼓噪声中也少有涉及到这个字眼的。人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为什么不随便找个工作,她为什么不换个便宜点的房子,以及她为什么不随便找个人嫁了。同时所有人都成了心理大师:抑郁、焦虑、自闭、社恐、应激反应,所以不是饿死的,是病死的……
都不错,既然女孩已经死了,于是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最大的可能,也是一个最简单的真相:她是一个被生下来,然后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孩子。
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满大街都是被生下来,然后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孩子。
以及一个最大的真相:他们有权选择不再挣扎。
在可能的饿死后面,这是更有可能的真相。
再一次谢天谢地,我们已经不习惯饿死这种事了,但我们可能需要习惯别的死法了。
不知道该谢谁?